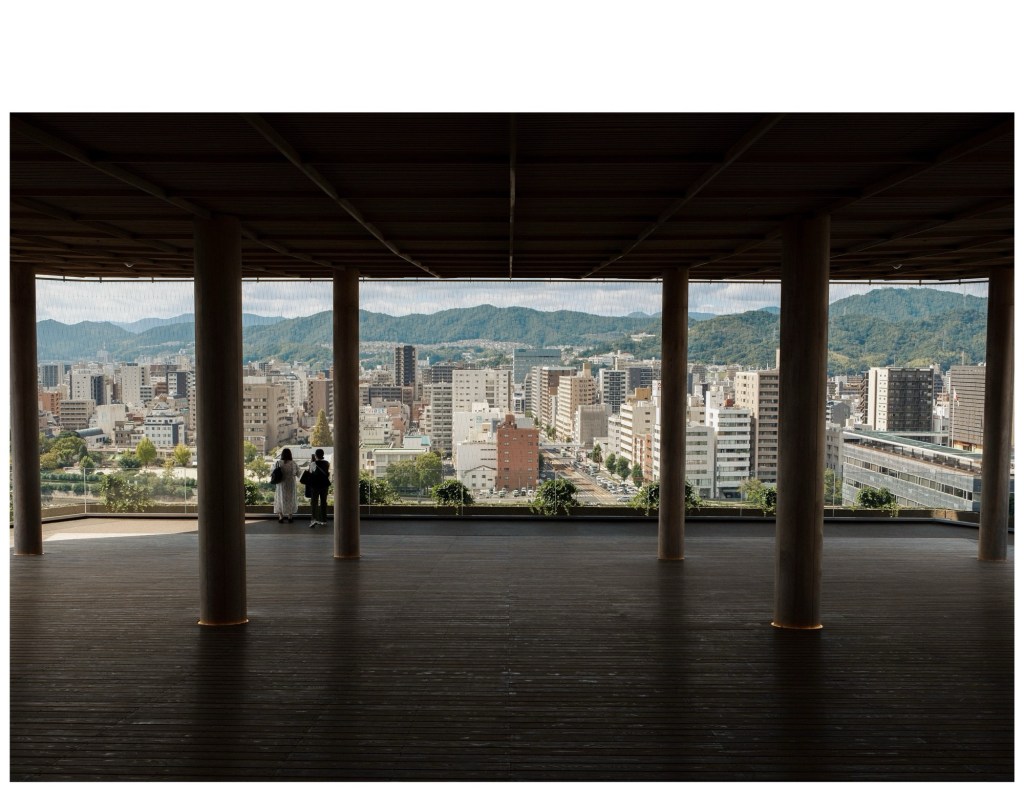
誰在雨中抵達廣島
抵着玻璃窗外的雨點
一而再張望天空的浮雲
尋找屬於黑色的元素
.
我攜着行李在便利店買一把雨傘
在店門前思考着還是乾脆用身體迎接雨水
.
離開廣島的時候天朗氣清
已經再沒有人談起昨天的天氣
我卻還把雨傘帶在身旁
最後把它留在城市中央的電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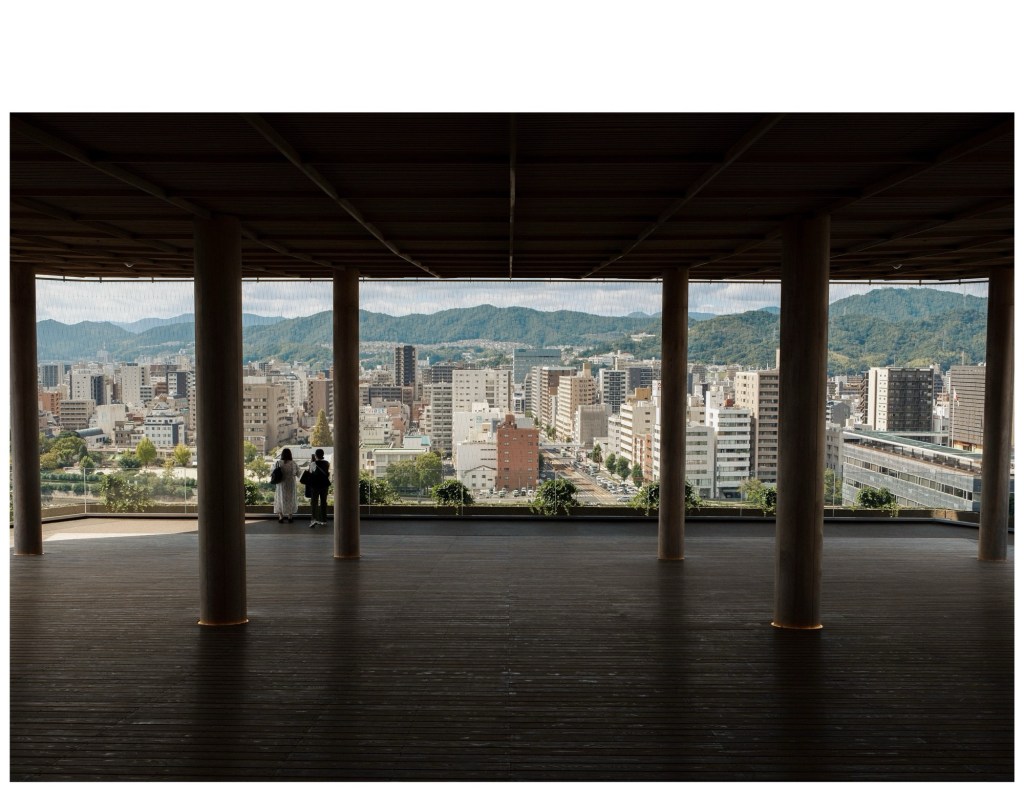
誰在雨中抵達廣島
抵着玻璃窗外的雨點
一而再張望天空的浮雲
尋找屬於黑色的元素
.
我攜着行李在便利店買一把雨傘
在店門前思考着還是乾脆用身體迎接雨水
.
離開廣島的時候天朗氣清
已經再沒有人談起昨天的天氣
我卻還把雨傘帶在身旁
最後把它留在城市中央的電車站
找不到入口和出口的XX停車場,大到像一個操場,但只能偶爾見到車輛駛過。每個人都在斜坡或樓梯之間步行,尋找但找不到入口和出口,停車場如同破舊的廢墟,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佈滿水氹、磚石,被遺棄的都市的一切。我看著人們在當中穿過的同時,找尋著自己的入口和出口。
我聽從公司的指令,到三樓的戲院裏,觀看C城領導人舉行的樣板戲播放活動,同事自成一角,沒有給我預留位置。我走了一圈,除了沒有人坐且看不到螢幕的第一排外,都沒有位置了,最後我在最頂的位置找到人手搬來的酒樓櫈上座下,鄰座是一些阿婆。
旋即離開。
到操場,像是學校早會的地方,同樣坐到最後。其後又被安排到台前,在眾人之下玩動作遊戲,早有三名參加者在等待著,台上附有床舖,我變回了小時候的自己,與右手邊的女孩一同嬉鬧,我們身後投影播放著童年時代的照片,看到很可愛的自己和很可愛的女孩,我們在眾目睽睽下,歡樂地渡過了時光。
我的夢被失去動力般的鬧鐘勉強叫醒,指針指著十時二分。遺下了對女孩的印象,夢中的冬菇頭女孩,究竟是我的情人,還是我夢中的阡䧥?我帶著一團疑問,開始了新的一天。
我已經不記得我有多久沒有外出進行跨年倒數這類活動。
在電視中,在社交媒體,在街上,每個人都期待新一年的到來,好像過去一年發生過的所有事件,都是無法承受的,大家都有急於背離的事物藏在後腦勺,等候著新出現的事物將它填滿及取代。
而時間的秒針卻分毫不差地,幾乎是以絕對均速地往前邁進。
去年這個時候我在做甚麼?許下怎樣的願望?或者是否真的曾經許下願望?是否在戀人的詢問下勉強許下一個為了應付答案的願望?我都無法記起。
在節日當中缺乏儀式感,這種人很容易在社會工作理論當中被標記為容易輕生的人群,但我亦很明確我人生的大部份時間並不是這種人。雖然也曾經想過死的部份,但終究我還是希望讓我曾經認識的人,知道我還是這個社會當中的一份子,雖然已不再在前線當中,但總算是這個社會的其中一塊齒輪。
前一段時間社會上似乎形成了一種輕生的風潮,或意念。我無從知道這種傾向到底如何,以及透過甚麼形式殖入那些人的心裏。但在官僚體系當中總是有會嘗試將這種現象解釋為不算嚴重、近乎已經是一種世界趨勢罷了的程度。
為甚麼夜裏的煙花會被視為一種慶祝度歲的象徵?我心裏在暗付著這種的問題的時候,我點起一根香煙,吸入肺部的同時,我看著火光由暗淡變成燈灰色的餘燼。
隔天起床吃午飯後,我到達了已經有一半商舖沒有營業的九十年代的小商場,商場當中只有四五間仍在營業,當中大部份店舖已被用作倉庫或展示店的店舖,店舖的發出的偏冷的燈光讓人懷念,售賣美國製火機以及普通女性飾物的店舖仍然在營業著。店舖的女東主見我是新手,立即花費時間向我講解使用火機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可能需要更換零件時可以再向她請教。
那樣的火機,我記憶中在二十多年前我的哥哥曾經擁有一個,他不在的時候我經常拿著它在手中把玩著,研究那光滑表面的裏頭究竟採用甚麼物質打造而成、握在手上時的冰冷觸感,以及打開上蓋時發出的標誌性的卡拆聲音,幾乎就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存在。
但最後那個火機也逃不過命運,它就像我的童年朋友一樣,在生命中留下標誌性的印記之後就消失掉。
現在我終於有空餘的錢將新的火機帶回家,鋼鐵一樣的外表下有用弧度曲線打磨過的紋理,我把它展示給我哥哥看。
他說:「我都有打算再買一個。」
基本上,我就是以上班、跑步、煮食、看書的模式渡過十一月。
戶外游泳池關閉,天氣突然之間墮入深秋、周遭的冷空氣激起我跑步的決心,向工作上的跑手前輩取得特別折扣卡、購買了MIZUNO WAVE RIDER 28之後,我就這樣在松山跑起來。而及後跑手每當見到我也特別關注我跑步的事情,甚至邀請我去參加除夕跑步比賽,但我拒絕了,因為我未適應以往跑步的節奏。不,應該是我要重新學習更具技巧的跑步方法,才能夠面對接下來的挑戰,一切要由最簡單的熱身動作及呼吸學起。
關於看書方面,我發現在電子通訊設備泛濫的現在,要保持專注性十分困難,於是我刪去了一切可能對我造成困擾的東西,例如過多的社交帳號,把它們從我的現實生活中分割出去。這樣,我就能每天投入專注讀書,把進入書本前所花的時間減低,將小說、實用書、社會科學等的各類不同的書籍填滿我的生命。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我已不再對文字產生恐懼和閱讀障礙,這種對文字的嘔吐感,是我在過去十多年來每日重複著單調乏味的記者工作和文字工作裏頭,在我的生命裏暗暗滋長的東西,簡直像職業病,一直揮之不去。現在,我的思緒彷彿像一隻戴在手上的機械腕錶一樣,一直轉動直至我的生命終結。同時我發現我寫作的思路漸入佳景,無論是議論文章、生活記事等等,都能一氣呵成。
這樣的日子,我不知道能持續多久,或者會不會當我的生活模式再次轉變後就自動摧毀?我不敢想象太多,我現在只知道,閱讀和跑步的日子,真好。
午後隨著大系線鐵道在長野一直往北進入大町市,秋天陰涼的天氣的開端還未開始。天氣微涼只因北方遠處蕩來的山風。
作為一座進入立山黑部前的中轉城鄉,這裏的發展恍似在二十年前就停滯了,應該說是二十年前就結束了。以溫泉鄉為賣點的大町市,唯一一條主要街道內,約一百間樓高一至兩層的店舖之中,以比例來推算,好像只有大約五間在營業。在轉角的商店街中,幽幽轉來一把男聲,好像這座城鄉的安魂曲,吟唱著衰敗命運的終結,我跟著這曲調,哼唱著粵語版《把歌談心》的歌詞,彷彿演唱者關淑怡就躲在某間陳舊店舖的角落裏應著和聲一樣。
街道上有幾個下課的一年級生,吃著雪糕之類的零食慢步回家,相信這些學生上課的地點應該隔著幾個鐵道站,因為大町的人口一看就知道不足以讓一所學校能往穩定的方向發展。
城鄉中大概只有兩間店與當代有所關連,一間是位於主幹道中央,以山泉水作招徠的手工啤酒商店,裏面有一半遊人都是以山系衣著為主,相信都是登山高手;另一間則是以介紹「北阿爾卑斯國際藝術祭」為主的實體店。因為早到了一星期的關係,我與大町市的藝術節注定無緣。
我隱約覺得這個城鄉的黑夜是深藍色的,當有遠風吹至田野的時候發出沙沙聲響。換個角度去看,城市的生活經常把人們塞滿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唯有在大町感受著這難能可貴的寧靜,欣賞大町晚間的獨特色調,幻想著隔天的登山之旅。

他曾經在一艘由南丫島開往中環的渡輪上拿出這本書,說借給她,然後一起觀賞那齣以此書為藍本的同名舞台劇。
好多年之後,除了平日的工作外,他倆已經甚少聯繫。他已經消失在她的生活裏面,她沒有向他交還這本書,他亦沒有再刻意提起。
再次相見,她已經結婚,但甚少與他人提起,甚至連社交網站上也沒有透露任何一則消息,就是這樣低調地成為了他人的妻子。
他自戀愛以後,收起了平日在社交網站中與他人活躍分享的生活瑣碎事,對其他朋友的生活也再不感興趣,包括她。
五年後他與戀人分開,一個人想回到最初自己的生活當中,卻發現一切也不再相同,他無法回到那個三十歲的自己的生活,他已經三十七歲,對生命中的大部份事情都不再抱有幻想,換句話說,他以減法的人生去盤算著將來可能遇到的事。
有一日,他在書店裡再次發現這本書,原來已經印刷至第三版了,即使再不是過往第一版那種精美的硬式封面質感,亦沒有影響他立即買下這本書,他拿起這本書,徑自回想起這些年來經歷過的一些事。
其後他在生命中遇上一位感情與工作經歷都與他相似的另一位女子,再次把這本書借給她,同樣地,沒有交還,像揮一拳到空氣之中,沒有得到回應。
這位女子在戀愛以後已經沒有再約他傾訴心事。但如果在一些場合遇上了,兩人就會在休息時段興高彩烈地交談,沒完沒了,兩人都說有空再約,但兩人都沒有付諸實行,兩人在這一點上,都驚人的相似。
他就是這樣除了上班以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做音樂、看小說、聽歌、玩電腦遊戲、跑步、游泳、架起投影機看電影,討厭人多的地方,各種興趣一直輪替,每天忙過不可開交。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他周遭的人的關係也在慢慢改變,只有他像斷線風箏一樣,獨自飄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到這樣的地方不好嗎?他一直問自己。
可能是很好的,但間中仍會感到孤獨,希望間中在身邊有可以傾訴的人,像天空中遇上第二隻同樣飄泊著的風箏一樣。
忽然間發現,O城晚上的燈光,已經不再被紫色的霓虹燈籠罩。
我在暗藍之中看到一夥星星,由於配戴著眼鏡的關係,我在有一點散光之中,看到星星呈不明飛行物的形狀靜止在天空中。
我單著左眼及右眼先後盯著那不明飛行物,散光隨之收縮,在確認它沒有異樣後,我呼出最後一口煙,把煙蒂弄熄。
人類總是善忘的,當O城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每個人都因為天空不再漆黑,夜裏看不到星星,而在私人部落格等半公開的領域咒罵掌權人如何不顧大自然而不惜一切破壞生態,像這個城市從來不屬於他們,從來沒有在當中分享到一分利益一樣嗤之以鼻,但當一切回復正常以後,就沒有人再談論掌權人如何順從民意,改邪歸正。
在這個人們熱愛把惡念無限放大的年代裏,大家都習慣把善意過濾,到底要如何才能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